裴浚牵着她从湖边石径绕出来,凤宁眼看前方停着一辆宫车,以为他要将她弄回宫,趁裴浚不备,飞快将手抽出,随后朝他屈膝,“臣女谢陛下帮扶之恩,夜深风凉,臣女恭送陛下。”
裴浚看着空空如也的手心,好一阵无语,他方才心正热乎着呢,她这么一抽,仿佛连他的心都给抽走,裴浚脸色都气青了。
他当然知道李凤宁怕什么,忍着怒咬牙道,
“朕送你回学馆。”
凤宁慢慢站直身子,偷偷瞄了他一眼,正对上他隐忍的脸色,讪讪没说话。
裴浚摇摇头,逼着自己不跟她计较,这才用力拽住她手腕,将人带上了宫车。
离开前,礼部一名官员追了出来。
今日赴宴的是礼部另一位侍郎石楠,他听闻汉康王世子御前跋扈被皇帝亲手击杀,给吓出一身冷汗,接下来如何安抚余下的王孙,如何给汉康王交待,都是个麻烦,于是他急急追出来,跪在马车一侧,先是认罪只道自己防备不周,随后请裴浚给个示下,接下来如何收场。
裴浚帘子都没掀,坐在宫车内听了石楠的话,面露不耐,
“这是你们礼部要琢磨的事。”
李凤宁在他底线上蹿下跳那么多回,他都没把她怎么着,能容忍旁人欺负她?
汉康王世子对李凤宁起意那一刻,就注定要死。
裴浚这话一落,韩玉便示意彭瑜赶车。
石楠起身对着远去的宫车再作了一揖, 得了这话,他算摸清了皇帝的态度,一个藩属小邦,甚至连个国家都称不上,皇帝压根没放在眼里。
石楠今年四十上下,正是意气风发大展宏图之时,礼部尚书袁士宏和左侍郎何楚生均年事已高,不出岔子下一届礼部尚书就该轮到他了。
他得在裴浚跟前好好表现。
石楠知道裴浚的脾气,不喜人小家子气,也没藏着掖着,除了隐去李凤宁,其余照实通传,只道汉康王世子藐视君威,被皇帝当场击杀,他通告其余王世子时,神情是无比傲慢嚣张。
大晋越强势,底下这些藩王更战战兢兢,至于汉康王那边,石楠也想好了主意。
直接遣人颁一道圣旨送去汉康王府邸,册封汉康王次子为世子,接不接旨就是汉康王的事了,接旨意味着他知趣,不接旨正好给了出兵的理由,附近其余藩国的儿子均在京城醉生梦死,谁乐意陪着汉康王跟皇帝为对,更何况汉康王底下还有个弟弟,他若不接旨,皇帝转手就能再出一道圣旨给其弟,届时便是内部残杀,大晋坐收渔翁之利。
汉康王除了接旨别无选择。
后来裴浚还可恨,杀了人家儿子,没有半分抚慰,反而孤立汉康王,舍了其余王国丰厚赏赐,独独申斥了汉康王,骂他教子无方,那些藩国得了好处越发生了看热闹的心思,无人声援汉康王,汉康王默默吃下这个哑巴亏,认命上书乞罪,甚至主动上贡珍品来“熄”皇帝的火。
一旦有人姿态放低,自有人争相效仿,这些藩国彻底臣服于裴浚的威赫之下, 裴浚就靠着这股狠劲,四平八稳料理了这桩事,顺带将藩属给收服了。此是后话。
再说裴浚这厢终于把姑娘安安稳稳送回跨院,进去时总算得姑娘一个好脸,给主动奉了一杯茶。
旁的不知,过去二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是没了。
裴浚坐着喝茶时,凤宁也能安静地陪坐一旁,甚至接过韩玉送来的手炉递给他。
裴浚将手炉还给李凤宁,让她暖着,自个儿捏着茶盏环顾一周。
他以为李凤宁的闺房已经够狭窄了,不成想这间小跨院的正房更窄,除了靠北的墙下搁着一张简单的床榻,南窗下一座狭窄的炕床,并几个锦杌小桌,再安置不下旁的。
这种逼仄之感,令他十分不适,原是一瞬都待不住,因为李凤宁,硬生生坐了一刻钟。
“朕在附近再给你置办个院子,挪个舒服的地儿住?”
凤宁笑眯眯摇头,“不必了,臣女觉着这里很好,窄是窄了些却极为怯意舒适,市井里的话陛下兴许没听过,旁人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,外头的宅子再大,臣女也不喜欢,就喜欢这一隅之地。”
拐着弯告诉他,不想住紫禁城那座最大的宅子。
裴浚抿着唇不吱声。
凤宁知道他恼了,也不做理会,起身道,“陛下饿了吧,臣女去给您煮几个饺子吃?”
冰天雪地裴浚舍不得她劳动,摇摇头,“不必,朕坐一会儿就走。”
又瞥了一眼那张卧榻,长不及八尺,能躺得下两人么?结实么?
凤宁注意到他的视线,微微僵了脸色,一声不吭垂下眸,假装没意会。
裴浚艰涩盯着她,“李凤宁,这儿还有比这屋子更大的地儿么?”
凤宁果断摇头。
裴浚闷闷不语。
留下来是不可能的,她满脸写着防备,皇帝现在也晓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,时辰不早,外头又催得紧,只能起身出门。
凤宁要送他出门,裴浚朝她摆手示意她留步,裹着一件灰氅大步越出门庭。
夜色如水,那道郎峻的身影仿佛踏水而来,又凌波而去。
凤宁就立在窗棂下,目送他出了小跨院,视线落在门檐,久久没有回神。
这样纠缠下去何时了。
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她还有能去的地儿吗?
他给不了她想要的。
她也永不会回头。
密密麻麻的酸楚注在心尖,最终盈成一眶泪,凤宁揉了揉眼,深吸一口气。
大不了就这么耗着。
以他的高傲,不会真把她掳进宫的,她不乐意做那种事他真能强来,强来的一时能强来一辈子?凤宁相信他不会。
裴浚回宫时心情并不好。
他拿捏得了所有人,唯独拿捏不了李凤宁。
她孤孤单单,一无所靠,一身傲骨,连性命也在所不惜。
换做是杨婉,王淑玉,哪怕是章佩佩,都可能因为家族荣耀委身于人,李凤宁不会。可恰恰,这些都是他最初相中她的原因。
她背后没有家族牵扯,唯一能捧出来的就是一颗心。
当初的倚仗,成了如今的掣肘。
而那颗心,也被他弄丢了。
从来自信满满的皇帝,这一夜罕见失眠。
*
翌日,下了一场小雪,天寒地冻,孩子们读书便显得艰难,虽说入了秋后,横厅两侧的窗牖均用厚重的纱帘包起来,可还是冷得渗人,一日有个小女孩病倒了,后来欧阳夫人自个儿也惹了风寒,两厢传染,学堂内充斥着此起彼伏的咳嗽声,无奈之下,夷学馆提前休学,待明年开春重启。
杨玉苏出嫁在即,凤宁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她备嫁,也能安安心心做翻译的生意。
这段时日,裴浚时常出现在学馆。
偶尔在书房陪她译书,见凤宁专注忙夷商会的事,不冷不快地将自己送来的诗经扔她案头,“这是经国重务,你是不是得先给朕译出来,再忙旁的?”
皇帝不懂民间疾苦,那晓得小商小贩的难处,一个单子没接好,可是丢饭碗的事,凤宁笑嘻嘻把书册揣怀里,“臣女心中有数,得了空会给您译。”
裴浚看出她敷衍的心思,却是摇头,严肃批评她,
“李凤宁,你可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,通译儒学典籍是大事,更能考验你的功底,能让你进益,你若只想挣点小银子就当朕没说这话,若要出息,你必得以译书为本。”
凤宁闻言微微怔了怔,当初她翻译第一册论语时, 乌先生教了她许多,紧接着翻译左传遇到更大的难关,乌先生更是逐字逐句给她释义,她收获良多,再到后来的大学中庸,她译起来就无比顺畅了。
他果然眼光独到,一针见血。
凤宁顿时羞愧难当,对他肃然起敬,“臣女谨遵圣命。”
他这人论本事真是无人能及,这一处凤宁是心服口服的。
只是,如今的李凤宁到底不同了。
她见了世面,也有自己的思量。
想了想又道,“陛下,话说回来,寻常那些商户送来的活计也很有益处,臣女平日翻译时,总能在其中熟知更多当地的通俗便语,也更了解蒙兀与波斯诸国,反过来能助我译书,所以臣女在想,两者皆不可误。”
裴浚意外地看着面前的女孩,她果然长进了,遇事不再人云亦云,不任凭旁人摆布,有自己独到的见解,他很欣慰,
“你若两手都抓好,他日必成大家。”
“大家”二字,令凤宁生出无限的向往与澎湃。
她一定要做到。
这大约是他在身旁的好处,他这个人要求极高,站得高又看得远,总能鞭策她前行。
“陛下放心,年前必定给您译好。”
相处明显有了转机。
只是皇帝陛下总是嫌屋子逼仄,每每来一趟眉峰皱得能夹死蚊子,凤宁笑吟吟立在门口,那眼神就仿佛在说,嫌弃就回你的皇宫去。
裴浚摇摇头,为了美人儿,只能屈就。不再急言令色, 不再冷语相向,甚至偶尔能主动给他烹一壶茶,下一趟厨,却决计不让他碰,偶然一次下雪地滑,他眼疾手快将人捞住,也一定是不着痕迹推开再去忙别的事。
裴浚心里怪不自在的,却也拿她没法子。
他现在明白了,这姑娘吃软不吃硬。
除了熬她,别无他法。
怎么熬能赶在年前将人接回宫呢?
*
一日杨玉苏试婚服,请凤宁回去给她掌掌眼,凤宁清晨早早登车回李府,李家经皇帝上次一顿敲打,如今元气大伤,个个瞧见凤宁别提多恭敬了,就连柳氏见了她都恨不得喊祖宗,心里再恨,也拗不过皇权,弹指间皇帝就能让她们阖家消失,可不得敬着凤宁。
凤宁一切照旧,没有仗势欺人,也不会心软接纳,面上见了打个招呼,私下独来独往。
这日陪着杨玉苏试了半日婚服,看着那大红鸳鸯通袖重工长褙,凤宁也忍不住生出几分艳羡,“每一身都好看,我都挑花眼了。”
杨玉苏嫁过去便是燕国公府的世子夫人,风光无极。
唯有正室娘子大婚之日可戴凤冠霞帔,婚服上准绣凤凰与牡丹。
那一身穿在身上,称得上流光溢彩。
杨玉苏后知后觉凤宁的身份,万分懊悔请她过来,二话不说将婚服脱了往旁边一扔,“哎呀,不试了,怪烦的,我陪你去温酒,咱们今日吃个烧鹅。”
凤宁才不许,睨了她一眼,“燕家嬷嬷在外头候着呢,你安心试吧,我去帮伯母核对嫁妆单子。”杨家只杨玉苏一个女儿,杨府尹又是出了名的疼女儿,名儿都舍不得唤,整日乖乖来乖乖去,快要搬出半个家当给杨玉苏做嫁妆,凤宁行至跨院,便见廊庑下琳琅满目堆了一百多抬嫁妆,这里头可不是虚的,件件均是好宝贝。
凤宁陪着杨夫人核对了一遍,杨夫人累了入了厢房喝茶,看着眉眼精致乖巧温顺的女孩,想起她身世可怜,竟是忍不住将她搂入怀里,
“孩子,你是不知,我心里也拿你当女儿疼,等你出嫁,我给你备嫁,赶明儿,选个吉日,你干脆认我和你杨伯父做干爹干娘,往后杨家就是你家。”
凤宁不习惯给人添麻烦,笑盈盈回,“凤儿就不给您添乱了,您若是真心疼凤儿,得了好吃的舍我一些便好。”
杨夫人一听这话,心疼地跟什么似的,“来来来,我现在就去后厨给你做烧鹅吃。”
凤宁在杨家用过午膳,下午又陪了一会儿,申时初刻回了乌先生的学堂。
她吩咐素心把自己捎来的一些箱盒,一道搬进院内。
她嗓音轻快,如灵莺婉转,浑然没注意有一辆低调的马车打后巷子经过。
裴浚原要绕去李府正门停车,恰恰掀帘一瞧,瞥见凤宁进了巷子里一处小门,他好奇,叫停马车,缓步跟了过去。
行至一道院墙旁,便听得里面传来欢声笑语。
乌先生的学堂,原是李府一个跨院,后来往里新建了一道围墙做隔,将原先的外墙凿开,筑了一段篱笆墙,篱笆墙并不高,只及一个寻常男子胸前,再于靠南一角开一扇门,便是独门独院。裴浚立在墙壁一角,目光越过篱笆,便能将横厅的光景收于眼底。
前几日下过雨雪,今日好不容易放了晴。
凤宁和素心要帮乌先生将被褥搬出来晾晒,乌先生哪里舍得她动手,连忙摆手,
“你难得回来一趟,就不必给为师操心,明个儿再晒不迟,来,坐下来喝一杯奶饮。”
凤宁便准素心回府探望爹娘,她陪着乌先生在廊下晒日头。
裴浚就看着那个在他面前防备,谨慎,勉强应承的女孩,捧着红彤彤的脸腮靠在凭几张望蓝空,她双眼懵嗔,神色前所未有惬意,想起什么歪着小脸与乌先生说,
“先生,陛下又给了我两册书,是礼记与诗经,我想专注将这两册书先译出来,其余的活计先生能否帮我担一担。”
乌先生正在给她煮羊乳茶,满口应好,他动作优雅娴熟,用烹茶的手艺煮出一壶羊乳,先给凤宁斟了一杯,凤宁闻着那香喷喷的气息,探手就要来捞,却被乌先生抬手一挡,
“小心,还烫着呢。”
只见乌先生盘腿坐了下来,又净了一遍手,拾起一个小勺子,慢腾腾在茶盏里搅动,恐自己气沫子脏了茶盏,脸离得老远,而凤宁呢,似乎熟悉了他的作派,安安分分在一旁等。
裴浚看到这一幕,缓缓眯起了眼。
乌先生的动作太过熟稔,而李凤宁也无比理所当然。
这说明什么,说明不是第一次,甚至可能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有过无数次。
回想李凤宁告诉过他,乌先生教她读书不下于十年。
所以这十年来,乌先生就是这么“照顾” 李凤宁的?
醋意不可抑制往上攀腾,裴浚神情绷得如同一片随时可以撕裂的帛。
羊乳茶就在这时,被推至李凤宁跟前,
乌先生笑容温切,“好了,可以喝了。”
凤宁像是乖乖等待喂养的小姑娘,高高兴兴捧起茶盏去尝。
这还没完,乌先生瞥见她下颚渗出一些乳渍,笑容宠溺地递过去一块帕子,
“急什么?为师能跟你抢?”
凤宁嘿嘿一笑,接过乌先生的帕子拭了拭下颚。
乌先生又将一小碟子葡萄干推至她眼前,
“你再加一勺这个试试,就是有些酸,你尝尝是否受得住?”
等伺候着小祖宗喝完羊乳茶,乌先生这才顾得上自个儿。
他的茶早已凉,抬袖做掩,很快一口饮尽。
不得不说,是位极为耐心,细心,体贴的男子。
如果对方不是李凤宁,裴浚应该会称赞他。
凤宁喝完,揉了揉圆滚滚的小肚,心满意足道,“先生手艺越发精进了。”
“哈哈哈,凤宁喜欢就好。”
凤宁喜欢就好裴浚听了这话,心情复杂地扯了扯唇角,将一个个字眼扎在心里。
凤宁这才想起捎来一个锦盒,无比得意地将之递过去,“这是这个月的进帐,先生帮我保管。”
乌先生从善如流接过来,又揽了揽衣袖,将锦盒打开,
“好,为师来瞧瞧,我们凤宁又挣了多少银子?”
还真就一张张银票在数。
“三两,五两,加起来八两,哦,这里还有个十两的银票,那就是十八两”
凤宁看着他一板一眼地数,乐得跟什么似的,
“我上月接了几个大单,那些商贾出手不俗,听闻我在礼部挂职,颇有亲近之意,放话随我开价.”
师徒二人你一言我一语,笑容被冬阳晕染,连时光渡在他们身上都变得柔软了些。
默契得谁也插不进去。
最后数清楚了,总共五百三十两银子,这对于凤宁来说,是一笔巨款。
凤宁和乌先生抵了一掌,看得出来极为高兴。
五百两,有时只是他一顿御膳的开销。
犯得着这么高兴?
不,他们高兴的不仅仅是银子金额,是那份靠自己安身立命的满足。
这么说,她挣得银子都是交予这位乌先生管着?
她就这么信任他?
他遣人查过这位乌先生,身份履历干干净净,像是凭空出现在京城的一个山野道人,无根无萍,就因为一次在酒楼无意中与夷邦人聊天,被经过的李巍听见,随后引以为知己,聘为西席在李府落脚。
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,顷刻便能卷款潜逃,让她所有辛苦付诸流水。她为什么不交给他呢这天底下还有谁能比得过他牢靠?还有谁敢觊觎天子之私.裴浚不能想下去,再想下去他怕自己肺管子要炸。
气嘛?
毋庸置疑。
醋嘛,那更不消说。
在这两种情绪之余,裴浚忽然意识到,在他看不见的地方,有个人这么疼她,她在他这里卑躬屈膝任劳任怨,指东不敢往西,在乌先生这里却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。
裴浚神色复杂吸了一口凉气,久久没有吭声。
而这时,门槛内那儒雅男子又忙不赢起身,
“哎呀,凤宁,时辰不早了,你歇一会儿,为师去和面待会给你做油泼面吃。”
“好嘞!”凤宁无比轻快地应着。
还能下厨?
君子远庖厨,儒家礼义在他这里倒成了空谈。
裴浚给气笑一声,笑意不及眼底。
他从来都不是忍气吞声的主,让他看着李凤宁跟旁人你侬我侬,没门。
修长挺拔的男人,面无表情抖了抖氅衣上沾的飞尘,冷着脸大步迈上台阶,叩响门扉。
作者有话要说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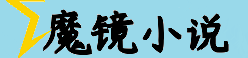 【请收藏魔镜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】
【请收藏魔镜小说 努力为你分享更多更好看的小说】